 名门出来的,身份不明的“花瓶”
名门出来的,身份不明的“花瓶”
我是三十年前开始对中国的陶瓷器进行研究的。
但是最让我难忘的是1998年10月的和“她”的相遇。
把它拿到我住所的,是一位与我有着二十
这件被K先生称为“青百合花瓶”的陶瓷器,是从大矶的I女士的茶具店买来的。I女士和K先生以前就是熟人。
那天I女士给好久没有见面的K先生展示了她刚买的物品:两件平安期的天皇的歌切、一件地方贵族向中国皇帝进贡的古铜器、一件带着折纸的井户茶碗,还有这件“青百合花瓶”,共五件。她告诉K先生,这些东西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家里的主人拿过来的。
在古美术商和古董商的行业里,有不泄漏卖主真实身份的规矩。就像现代社会经常说的“个人隐私保护”。其实在这个业界里,从很久以前就一直遵守着这样的规矩。
这些都是有很高价值的物品,一旦泄露了卖主的真实身份,也许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对于买主来说,物品的出处对鉴定其价值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很想知道卖主的情况,但规矩就是规矩。
所以,I女士并没有将出处告诉K先生。也许这些物品来自非同寻常的名门望族,她还是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口吻对K先生说:“这可是好几百年前的东西呀!”
K先生当即买了五件之中的古铜器、井户茶碗、青百合花瓶三件。古铜器和井户茶碗,读一下上面的铭文就知道它们的身份了,但是陶瓷器却无从查考。这就是“青百合花瓶”。
K先生感觉这绝不是一般的东西,于是就带到我这里来了。
从没见过类似的作品
K先生拿过来的“青百合花瓶”一定是件非常古老的物品,并且绝不是现代有意制作的赝品。因为K先生和我都不曾看到过和此品相似的作品。
我还要说的是,我们两个人都是古陶瓷器研究的专家,都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就是这样自负的我和K先生两个人过去都没有见过,所以认为这件作品绝不是为了骗钱而做的赝品。谁会没事闲着做这种谁也不知是什么东西的“赝品”,这样做能有什么意义呢?
毫无疑问,它是我们过去未曾见过的真正的“名品”。但是仍然又有疑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关于 制作年代 ,当初K先生认为这是五六百年前的明代的作品,而我却感觉这是比明代更早上一二百年的宋代的作品。但是不论明代还是宋代,都没有与此类似的陶瓷器在世人面前出现过。
中国的宋代,有汝窑、钧窑、定窑等烧制过历史名品的名窑,但是“青百合花瓶”与哪个窑的特征都不符。除此而外,再与龙泉窑、越州窑等所有历史名窑的作品一一进行比较,和这件陶瓷器类似的窑仍然没有找到。也就是说鉴定陶瓷器来历的重要的一点――“窑”,也无法确定。
像这样美仑美奂又布满谜团的古陶瓷器,有可能成震惊世界的新发现呢。要想追究其年代,一定要花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K先生对我说:“我已经没有再花上几年时间去研究它的力气了,以后的事情交给你了。”K先生是年过古稀之人了,那情形像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一样。从那时起,我接受了这个“青百合花瓶”,开始了找寻它真正身份的漫长旅程。
中国陶瓷器史上最大的谜
这之后,我搜集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最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令我自己都吃惊的假设。
在中国陶瓷器的历史上,有一个至今都未曾解开的谜团。它被称为“世界陶瓷器史上的奇迹”,虽然是官窑,却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它,碰到过它,是“奇幻般的至宝”。
因为没有发现过这个官窑的实物,所以它的存在与否,多有争论。但是在文献上确有记载。在数百年前就曾有众多的研究者、古董商、收藏家熬红了眼睛千辛万苦地进行寻找,可最终连个影子也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的不仅仅是成品,窑址也没有找到,甚至连一个小碎片也没有。也因此,在中国古代陶瓷器研究专家中,不少人对此窑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这就是后周的官窑――柴窑。
柴窑的年代大约是距今1050年前,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五代十国”的末期,在日本史上来说,是平安时代的中期。
在这个时期,作为“五代”中的一个朝代,从951年开始到960年结束的是“后周”。954年,继承了太祖郭威皇位的柴荣皇帝(世宗),被称为五代之中唯一的名君。柴窑作为他的官窑,大概也因此而得名。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很多,但是以皇帝的姓来命名的只有柴窑。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后周的官窑柴窑,是从柴荣皇帝在位的954年开始到959年,仅仅存在了5年时间。文献记载确凿的话,没有发现柴窑遗址就可以理解了。既然存在的时间短暂,数量必定十分稀少,又是一千年前制造的东西了,所以柴窑的作品就是“奇幻般的至宝了”。
牛津大学的科学鉴定
2005年3月份,我决定把“青百合花瓶”拿到牛津大学去做科学鉴定。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出“热致冷光法”的大学,但是现在进行鉴定的只是其下一个独立法人机构。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权威和最多的经验,这家机构接受过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博物馆等诸多著名博物馆的鉴定委托。日本进行科学鉴定时,也多是委托这里。因此,我也想在这里解决这件名器的年代问题。介绍我来这里的是美国圣旧金山博物馆,这所博物馆也是经常委托这里做科学鉴定的。
话说回来,这个决定并不是我主动做出的,而是和我一起进行“青百合花瓶”研究的朋友们提出的意见。
“对中先生,现在除了把花瓶拿到牛津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历史研究和文化考察都已经进行的十分透彻了不是吗?所有的特征都和柴窑的瓷器一致,我们也知道有几乎足以乱真的仿古做法。仍然否认这樽花瓶是柴窑的人,所提出的问题不就只有制作年份了吗?既然如此,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来鉴定出它的诞生年代,才能得到世界的承认。假如能够证明这个花瓶诞生的年代与柴窑同期,那就可以作为这件瓷器是柴窑出产的绝对证明了。”
他说的确实很正确。但是,我踌躇了。的确,能用科学鉴定法得出制作的年代和柴窑一致的结论,必然是最有力的“物证”,但是可能性却不怎么高。就算“青百合花瓶”是柴窑的作品,得出的测定值不能成为证据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
但是,在我犹豫这个犹豫那个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并没有等待我的答复,自行联络了牛津,自行进行了科学鉴定的预约,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当然也可以取消预约,但这时我已经做出了决定。如他所说,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如果想再进展一步,只有求助于科学鉴定了。
因此,我将“青百合花瓶”交给那位朋友,请他带到牛津去了。
 一个月后的“结果发布”
一个月后的“结果发布”
后周官窑柴窑进行生产的时期,是世宗柴荣在位的954-959年。自然,我们将申请检查的预测值设定为这个年代。
但是测定结果并不会十分准确。再过个十几年,也许测定精度可以提高到那种程度,现阶段的技术是有它的局限的,无论怎样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虽然不能严格界定出准确的制作年代,在允许范围内,只要包含这五年就算是合格了。
距离检查结果出来还有一个月。对于委托人来说,这段时间再漫长不过了。在此期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祈祷着结果的发布,整天郁郁度日罢了。我度过了这么一段无心工作、无法安眠的日子。这样的等待对人的健康真是无益啊。
一个月总算到了――
已经回国的朋友和我联系:“牛津的通知书到了”。我问:“结果如何?”对方回答说还没拆封呢。还说自己一个人先看的话太不够意思了,不如找个时间咱们见个面然后一起看吧。虽然我很感激他这份心意,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也不敢一个人去确认这结果。
我俩约在经常去的家庭餐馆里见面。朋友手里捏着那封未拆开的信件。
“可以了吗?”
“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我苦笑着回答说。既希望马上就打开,又想再等一会儿,心情十分复杂。这里边装的是谁都没有办法提出异议的决定性的测定结果。看了这个就没有退路了。如果出现的不是期待中的结果,就算“当成没看过吧”,也只能是自我安慰了。
但是又不能不看。没想到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却还这么焦虑地等待着“成绩发布”的结果。朋友正在启封的手指和我的心都在颤抖。
从信封里取出来的鉴定书左上方贴着“青百合花瓶”的照片。“A BLUE GLAZED VASE”――是它的英文名字。检查结果在那之下好几行的鉴定书中间。
THE DATE OF LAST FIRING WAS: BETWEEN 700 AND 1100YEARS AGO
一瞬间,我感觉时间都停止了。我沉默着,与朋友对视了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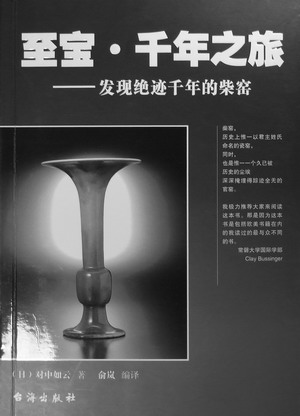 这樽蓝色花瓶是七百年到一千一百年间的时间段内烧制的。
这樽蓝色花瓶是七百年到一千一百年间的时间段内烧制的。
柴窑的时代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牛津的关联科学机构正式认定了我们的预测与科学鉴定并不矛盾。
我和朋友用力握了握手,并给另一位朋友打电话。电话是打给最先把“青百合花瓶”拿到我这里来的K先生的。
“K先生,太好了。牛津认定这件作品是七百到一千一百年前的作品。”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但是声音好像很激动。
“对中先生,你不是在哭吧?”
不过在我听来,说这话的K先生倒更像是在哭。
(摘自《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台海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定价:29.80元)
